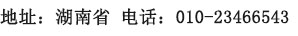宋代以科举取士构建官僚集团,南方文化迅速上升,福建、江西、四川等地都成为书香之地,在科举上优势突显,成绩斐然。这引起身居权力中心的北方人的恐慌,为维护既得利益,从政治上加以打压南方就成了宋初新政之一。
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曾以诏书知会御史台要求审查全国官员的籍贯,严禁南方人在本道担任知州、通判以及转运使等官职。宋代前期的执政集团一贯看不起南方人,他们编造了一个太祖曾定下不准南人为相的祖宗旧制,到真宗朝,名相寇准(陕西渭南人)和王旦(山东莘县人)等大批北方士大夫仍然对南人蔑视有加,在南方入宋已近40年后,寇准仍称南方人为下国人。
南人自然不甘北人之压制,在真宗朝终于通过努力进人权力中枢,并一度权倾天下。然而,其中部分人先是采取附会宋真宗天书封禅的方式来奉迎皇帝的造神运动以取得权力,于是南人又被舆论定格为有才无德的小人。在这些“小人”中,官职最低的福建人林特成为舆论所言的典型的有才无德型人物。此后,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北方士大夫就尽量在宣传上把福建人等同于小人,将福建士大夫排挤出朝廷的权力中心之外,这一过程在神宗年间达到顶峰。
在明神宗年间的变法与不变法之争中,福建新进士人借参与变法大量涌入权力中心,吕惠卿(泉州)、章惇(南平)、蔡确(泉州)、蔡京(莆田)、蔡卞(莆田)等福建人相继成为变法派的骨干,而反变法势力虽然一度失势于权力中心,但他们凭借把持政治话语权的地位,极力塑造福建人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的舆论。
尽管宋代北人士大夫竭力使闽人边缘化并未能阻止闽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他们几乎成功了,《宋史》中《奸臣传》的北宋部分就几乎成了福建人的专版,《奸臣传》总共20人中,福建就占了9人。
在宋朝,四川人被北方人称为“川藞子”,也即说四川人粗野放诞,不遵礼法,是一些好乱易动的奸恶刁民。把四川描绘成奸民险地的梁周翰,到蜀地为官后对蜀民大搞严刑峻法,把人活活打死之后,仍理直气壮。余靖代表朝廷拟写的给益州(今成都市)知州文彦博的制书,居然要他到蜀地后“勿贪宽厚之名”,这就是公然鼓励和敦促地方官到四川搞暴政了。可见,蜀地被塑造成一个危乱之地后,暴政在四川的推行就具有了合法性和习惯性。
明代正德年间的内阁大学士、任过吏部尚书的大官焦芳,曾不遗余力地推行地域歧视。这位大学士是河南泌阳人(今河南驻马店市泌阳县城南草店村)人,他歧视的是江西人。
恰好当时有一个南洋的小国满剌加(在今马来西亚境内)派使臣来大明朝贡。一个叫亚刘的使臣,本是江西万安人,原名萧明举,在中国犯了罪流亡海外,改名换姓,没想到混得不错,爬上去了,当了使臣。这个人和另一个满剌加土生土长的使臣端亚智同来天朝,途中他密谋到渤泥国(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的古国)索取财物,也许端亚智认为这破坏了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同意擅自行动。这个萧明举便把端亚智给杀了。这当然是件大事,作为宗主国大明朝不能不过问。
有大臣立马上了奏本,焦芳看完奏本,立刻如获至宝,把萧明举的犯罪行为和他的籍贯联系起来,大肆攻击江西人,还把古人拉出来给自己的地域歧视作理论根据,他说:“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勿滥用江西人。”
焦芳不仅仅歧视江西人,对其他南方人一并歧视,就是谈到古人也忘不了诋毁南方人,他专门作《南人不可为相图》进献给权宦刘瑾。因为刘瑾是陕西兴平人,他拍马屁增加了陕西乡试名额,当然也不忘给自己的家乡河南谋福利,他将老家河南的乡试名额增至95人额。
(据《羊城晚报》赖晨/文)
文摘周报,爱的陪伴。
关爱老人,给他们订一份《文摘周报》吧!
欢迎订阅文摘周报
《文摘周报》全年99期,年全年订价元
订阅,邮发代号61-10
在线订阅请访问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